我的母亲冯丽是标准的老南通,出嫁前就住在寺街沿着环西路的街边大宅子里。外公外婆都是那个年代特别能干的人,尤其是外婆把整个一大家子操持的稳稳妥妥。母亲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出生的,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出生在最困难的那几年,母亲自然成了家里众星拱月,共同呵护的心肝儿。吃不饱的年份家里再平添一口,无疑是雪上加霜,舅舅就晚上跑去乡下偷菜,回来偷偷的熬小米菜粥给妹妹吃。外婆的家教极严厉,把舅舅打的两天没法坐凳子。外婆常念叨这些往事,说起来眼里总是噙着泪花儿。母亲就是一直这样被疼爱的长大,家务活哥哥和姐姐从来都不舍得让这个宝贝妹妹做。母亲的“手巧”也就是在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培养起来的。听以前的老街坊讲,母亲在十几岁的时候做针线的手艺就已经在那条弄堂里小有名气,被街坊们亲切的称为“小绣娘”,她常常对着书上的版子就能做出件漂亮的衣裳,每件作品还绣上自己创意的各式花纹。母亲“手艺”的最早受益者是我的两个表哥,舅舅和姨妈都是也都是生的儿子,母亲总能变着花样的给两个小男孩儿做漂亮的衣裤,绣上各种孩子们喜欢的卡通人物。以至于后来表哥们的书包每年都要拿回来给母亲绣上最新流行的图案,总能高兴好一阵子。
母亲十七岁插队农村,原本两年以后可以接替外公供电局的工作,但她却始终怀揣这一颗“绣娘”的梦,毅然放弃了那时候看来就很不错的安稳工作,而凭借自己的一双“巧手”顺利的进了当时的工艺美术研究所。从此母亲走上了沈绣艺术的传承之路。
总之从我记事起,母亲就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刺绣艺人了,我也无从知晓这之间的几年她是如何苦练自己的内功,只记得我童年的那段时光几乎每一个回忆的点滴都洒落在研究所。小时候我身体不是很好。母亲说,我刚出生的那几年她正好在搞“作品承包”,也就是那时候几个特别要强的姑娘没日没夜的搞创作、比成果,而一定程度忽略了对我的照顾。这也是她到现在都觉得特别亏欠我的地方,以至于后来母亲几乎寸步不离的照看着我。直到我正式上小学之前,我的几乎每天都是伴她左右。现在想起来很感谢那段时光,让我从小就能耳濡目染各种文化艺术,对我以后的发展和择业也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沈绣、风筝、剪纸、蓝印花布、彩色扎染…研究所几乎涵盖了大部分现在的手工艺非遗项目。很多人选择各个领域都试一试,而母亲却是从进所开始,始终如一的从事沈绣的研究和创作工作,“小绣娘”的梦想一直扎根在母亲的心里。
母亲是沈绣的第四代传人,刺绣这门手艺和很多已经失传的技艺一样,需要手把手的衣钵相传,母亲那时候正处于技艺成长最有利的时期,她自己主动找到当时老艺人们,拜师求教。那段时间,她几乎是废寝忘食的研究各种配线技巧,各类针法。
有一年夏天特别热,绣房的姑娘们很难在闷热的绣房里长时间工作,熬到下班时间基本都收拾回家了,但母亲从来都不会准时。有天直到很晚她才到楼下的花园里接我,我不知道原因,只是看到她显然是哭过了。后来到了懂事点的年纪再向母亲问起那天的情形,才知道那天非常闷热,但她一直坚持要把作品收尾才走,结果没留意几滴汗水滴在了绣品的关键部位上,汗水对刺绣作品是很严重的破坏,常常会留下明显的印记。母亲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所以那幅作品给她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十几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个故事母亲依旧唏嘘不已,或许对于她而言,那是她最铭心刻骨的记忆,她是如此的视艺术为生命。
九十年代末的全国下岗大潮卷席南通。由于种种原因,研究所终究还是走向了衰落,母亲也成为了众多下岗职工中的一员,很多人建议她凭自己的好手艺完全可以进一家不错的单位,但她还是坚持在家创作,那段时间父母的工作情况都不理想,家里的生活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母亲是个非常顾家的女人,每天操劳各种家务,再做一些可以养家的手艺活,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沈绣的研究和创作了,每天都会搞到很晚。一盏台灯,一个简陋的绣台就伴着母亲在深夜一丝一线的搞作品研究。曾今几度半夜醒来仍能看到阳台上昏黄的灯光。为了不影响家人的休息,母亲一到晚上就把绣台搬到阳台上,即使在最冷的寒冬夜亦是如此。我曾问过她能不能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了,母亲只是坚定的告诉我:“如果都这么想,那这门手艺就真的断掉了,研究所解散了,沈绣不能散。”这句话让我一直铭记。

从在研究所到下岗自主创作,母亲常庆幸自己并不孤独,一路走来,总有知己相伴。李锦云对于母亲而言,亦师亦友。早年她们便是研究所的同事。李锦云是老一辈的沈绣传承人,深得沈绣技艺的精髓,尤以人物肖像题材的作品见长,其作品早已蜚声业内。母亲和李锦云的师徒缘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一次作品的小组分析会让她们对作品的创作构思产生了分歧。母亲是个直爽性子,虽然面对的是老艺人,还是坚持自己的构思,现场演示起自己的走线构思。这在外界看来的“挑战权威”非但没有让李锦云生气,反而大大赞赏了母亲对沈绣的大胆创新思路,这也促成了她们之后延续至今的坚实友谊。对于母亲而言,李锦云更是恩师,母亲这一辈的传承人很少能够接触到“人物肖像绣”的题材作品,在李锦云手把手的传授下,给母亲生动的补上了“肖像绣”这一课,母亲对于刺绣的理解能力极强,很快便能够应用的得心应手。母亲下岗自主创作的这段时间,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和李锦云一起讨论作品的构思和技法,甚至常常两人会为一点小细节发生争论。现在想来,正是她们对于艺术的这份执着和苛求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沈绣精品。

母亲最高兴的时候莫过于自己的作品受到肯定,母亲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行业里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作品得到了来自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很多国内外收藏家的青睐和赞誉。即便如此,母亲从来不高价出售自己的作品,她常笑说自己永远做不成商人,艺术沾上商业就很难再纯净了。近几年她一直投身于沈绣的传承教学中,能够真正的把这门艺术传下去是她最大的心愿。

说到与“国礼”的结缘,不得不提到卜元。沈寿艺术馆的馆长卜元可以说是母亲的伯乐。卜馆长也是一直从事着沈绣的研究工作,他对于艺术的敬畏和对沈绣的执着也是我一直敬佩的。在现今到处充斥着商业化运作,各种打着艺术名号做生意的浮躁时代,卜元是真正为南通的沈绣传人们守住了最后一方净土。我的母亲也受馆长的邀请,从2002年至今一直担任沈寿艺术馆的艺术顾问的工作。
2011年3月,沈寿艺术馆接到绣制送给比利时国王的“国礼”的光荣任务。南通市外事办钮启贤主任与沈绣艺术馆馆长卜元几上北京,认真听取要求。卜元从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夫妇的多幅生活片照中,精心挑选了素材作为绣稿,并亲自绘制画稿,进行二次创作。由李锦云和我的母亲担任《比利时国王夫妇肖像》的国礼绣制工作。这幅作品的意义非同小可,母亲和李锦云在其后的七个月时间里全力投入到作品的绣制之中,最终当现任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接到沈绣《比利时国王夫妇肖像》的国礼时,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而《普京总统肖像》则是继《比利时国王夫妇肖像》之后,沈寿艺术馆接到的又一次“国礼”重任!早在去年的12月初,南通沈寿艺术馆就接到了这份神圣的工作。月底,卜馆长就飞赴北京商讨方案。我的母亲再次很荣幸的参与到这次国礼的绣制中。由于这次是高度保密的工作,在作品创作的三个月时间里,母亲也只是简单的和我说去参加一个封闭运作的项目。没有想到三个月之后,母亲所在的创作团队竟然再次给创造了如此惊叹的“国礼”,而这次也大大缩短了绣制的时间。正如母亲说的那样,每一幅作品都是饱含着创作者的感情的,或许正是由于她们这一代人从小对中俄情谊的深刻感悟,才会将这幅国礼打造的如此生动传神!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母亲面对镜头有些激动。新闻播出后,南通“国礼”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热点新闻。我知道母亲是幸福的,我能理解她那份甚至想像当年那样大哭一场的激动。默默耕耘了数十载,她们不为名利,只是为了今天这样获得肯定,让更多的人了解沈绣,给她更大的勇气在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我知道,母亲早已不能离开沈绣,当年的“小绣娘”的梦想已经悄然绽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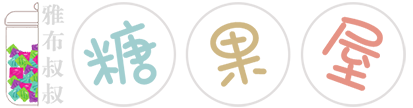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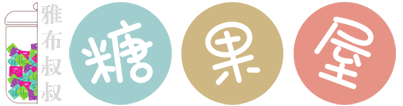

1 条评论
你好,看完感觉高大上